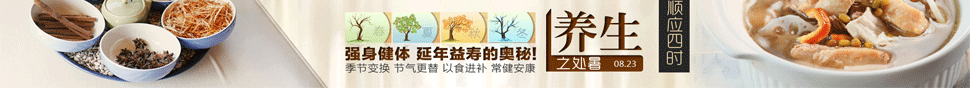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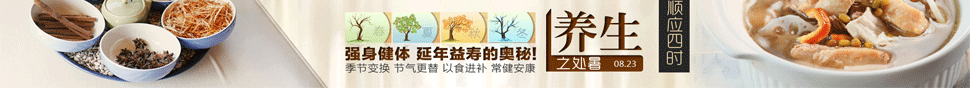
文
杨维忠
年5月29日
身处在社会变迁的时代,不断涌出的新鲜事物让我们应接不暇。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中,伴随我们一起成长的那一道道风景,在推陈出新的大潮中被慢慢湮没。以至于,我们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一段视频,抑或拍下几张照片。
然而,这业已消失的风景早已深深印刻在生命的底片上,经历了岁月的打磨后愈加清晰。浮现在脑海里的一花一草、一土一石,仿佛都触手可及。
这就是蝎子岭,宛如一只巨蟹横卧在河东的岭坡上,承载着少年的欢乐,承载着青年的思念,也承载着人到中年的丝丝忧伤……
01
附近村庄的人都把这里叫亭子崖,“崖”的读音是yái,是指陡坡。因为有“亭子”两个字,这里就显得清秀雅致。事实上,我们从来没见过这里的亭子。甚至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也从未提起过这里的亭子。
旧时的亭子会修建在荒郊野外,便于行人过客落脚休息。可以想象,很久以前,这一带人烟稀少。远行的人走到这里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。爬上高高的崖头,坐在亭下歇歇脚。吹吹凉风,喝杯热茶,顺带欣赏这秀美的风景。若是如此,我们脚下的羊肠小道该算作一条古道,重叠着前人无数的脚印。
及至后来,沿河两岸在这一带聚集了数万口人。人多了,就开始向大自然索要资源。于是,原始的山坡被开垦成一块块梯田。而石层覆盖的地方没有开垦价值,就保留了下来。也是在不经意间,这一带被改造成蝎子的形状。
蝎子岭因此而得名。
02
据说在远古时候,这里曾有长成大山的势头。有一天,泰山上的碧霞元君,也就是百姓口中的泰山老奶奶从这走过,看到了即将成山的蝎子岭。她说,这一带周围都是山,蝎子岭就不需要成山了。于是,她在岭顶踩了一脚,蝎子岭就停止了生长。
小时候听了这个故事,内心有些遗憾,总想着在蝎子岭顶会突兀立起一座高山。小时候没爬过山,不知道山是什么样子。等长大了爬山,总找不到内心想象的山的样子。直到前几年在武夷山下的九曲溪上漂流的时候,蓦然看到水边拔地而起的玉女峰,内心竟生出莫名的亲切感。许久以后才明白,这就是小时候想象的蝎子岭。按照有果必有因的观点去推论,也许能长成山的蝎子岭,就该如玉女峰般突兀而起,挺拔秀丽。
03
蝎子岭最南端是这一带的制高点,站在这里往西看,遥遥相对的是相隔十几里地的西岭。村里的老人说,很久很久以前,我们西边有一条大江。我们这边是东岸,西岭则是西岸。后来水神用巨斧在南山劈了一道口子,水泄了出去。从此,河床变成了小平原。
这条江还牵连着一个历史人物——战神伍子胥。据说春秋末年,伍子胥来此渡江。江面宽十余里,没有桥梁,也没找到船渡。情急之下,伍子胥扬鞭催马,直接飞跃到对岸。蝎子岭往北行十余里,有一个两千多年的古村叫垂杨。垂杨有伍子胥庙,还有伍子胥打马过江处的碑碣。
这里有没有媲美长江的大河,很难去考证。但小的时候在蝎子岭上玩耍,随手就能挖到镶嵌着田螺化石的石块。用沧海桑田的眼光去看,蝎子岭曾经是水岸,甚或是水底的丘陵。
记得那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《黄河象》,知道了化石的成因和价值,所以就挖了很多收藏。可惜的是,多年后一块也找不到了。也许城市化的大潮席卷到蝎子岭上,这些化石也会和普通石块头一样被碾碎,与一个时代一起消失。
04
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夏天,阴雨绵绵,连月不开。用祖辈的话说,叫做“阴晴四十五天”。坡上的水下渗,在街道、胡同里形成一个个迷你的泉眼。有几段土坯墙浸泡在水中,几近坍塌。
突然有一天,小村上空响起一声惊雷。紧接着,蝎子岭上传来山崩地裂的巨响。
天晴了,人们赶到蝎子岭,发现顶端的西侧出现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。夹杂着泥土的水从边缘涌出,形成瀑布。
又过了几天,涌出的水水势渐缓,水也变得清澈。
彼时,远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正浓。在中国,先是袁世凯复辟称帝,接着便是护国运动、护法运动。十里八乡的百姓都在秉承着耕读继世的传统,过着封闭自足的生活。他们无从了解国际大事、国家大事,却很快知道了蝎子岭上出现的奇观。据说口镇、港里的人骑着毛驴,专程赶到这里观看。
再后来,这一奇观被赋予了更为神奇的故事:蛟龙下蛋!蛟龙劈开一道裂口,把龙蛋埋在里面。七十年后,蛟龙会破壳而出……
没有人知道为何是七十年,也没有人知道蛟龙出壳时会发生什么。到了第二年,裂缝里不再溢水,但依旧看不到底。有位爷爷小时候在裂缝边玩耍,不小心滑了下去。当时的裂缝很窄,成年人无法下底,只能递下一条棉绳,把他拽了上来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蛟龙下蛋的故事慢慢被淡忘。也只有我们村里的人谨记着这个传说,期待着蛟龙出壳。
村里寿限最长的爷爷说,“蛟龙下蛋”那一年他十七岁。七十年后,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。八十七岁的他身体依然健壮,十一二岁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摸爬滚打。
那时候,裂缝的西侧坍塌到了崖下,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土堆。裂缝中央露出红褐色的块状土层。而东边一侧,则是五六米高的崖壁。崖壁虽然陡峭,但偶或露出一段树根,偶或凸出一角石棱,就足以让我们踩在上面,如履平地。
05
又过了几年,裂缝底部被人开垦,种上了几畦高粱。而传说中的蛟龙,依然没有破壳的迹象。
有时我会想,当年惊雷劈开裂缝,是蛟龙下蛋,还是蛟龙出渊?记得小时候去姥姥家,有位远房的姥爷曾讲过这段故事。不过他说的不是蛟龙下蛋,而是“出蛟”。
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,一条蛟龙破壳后,一道惊雷劈开压在身上的土层,腾空而去。如此看来,这条蛟龙也算是我们的同乡,或者说是邻居。历经百年,蛟龙也该修成正果了吧?如果有一天它回到破壳出生的地方,是否也会因为蝎子岭的容貌不再而感到失落?
06
蝎子岭上的蝎子很多,但不是我亲眼所见。有一年暑假,南乡的一位老者来这里采药。口渴了,就来我家讨水喝。我冲了一壶老干烘,和他坐在天井里一起喝茶。他常年在各地采药,见多识广,给我讲了很多故事。说到蝎子岭,他说这里的蝎子特别多。如果捉蝎子,一上午就能捉很多。
我说蝎子岭上没有蝎子。他笑笑说,你们可能不捉蝎子,所以不注意。
其实不止是在蝎子岭上没见过蝎子,在家里也没见过。我没见过,不代表没有。那时候偶尔会听说谁在门外晒柴火,搂出一只大蝎子。也或者谁被蝎子蜇了,疼得一宿睡不着。
有一年初春,二伯家的堂哥跑到蝎子岭上扒石头,发现了一只尚未出蛰的蝎子。蝎子已经成年,但因为在土下蛰伏了一冬,通体呈半透明的乳白色。估计他是第一次见蝎子,就用一个塑料袋装起来,挂在自己的腰带上。他先是一路小跑跑到大伯家炫耀,又跑到我家让我看。
因为我此前没见过蝎子,所以看得很仔细。那只蝎子身体很软,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偶尔微微翘一翘尾巴,证明自己是活的。堂哥几次让我用手摸摸,我始终没敢。
想想我们在姗姗学步的时候,就在蝎子岭上玩耍,却从未遇到过蝎子,大抵是山神的护佑吧。
07
蝎子岭很美,那是一种深沉的美。
这里的大多数区域,地表是一层白石。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和雨淋,白石层上长满暗绿色的苔藓。遇到天旱的时候,苔藓脱水变成深灰色。
这里的植被大多是多年生的,且成长缓慢。小指粗细的枝干,大都呈铁黑色。再加上匍匐在地上的深绿色的藤蔓植物,让这一片区域整体呈深色。与周边黄土地上长出的绿油油的庄稼,形成明显的色彩差异。
这里的物种很多,也很奇特。
春天来了,一丛绿意从石缝里溢出,就如枯木发荣般夺目。到了夏天,这里就成了花的海洋。有紫红色的小碎花,有蓝紫色的小灯笼,也有鹅黄色的小花朵点缀一地金黄。到了秋天,成熟的酸枣在险峻的峭壁上招摇。也只有大雪覆盖的冬天,这里才会与近处的农田、远方的高山融为一体。
08
大人很少会在这玩,也就造成了在植被认知上的断层。那些花花草草,都是小孩子间用自己的认知去命名的。
最先认识的是茅草上的“谷荻”,不过我们习惯称之为“谷嘚”。开春不久,绿草尚未返青,谷荻就已经冒出了芽。蹲在地上一小会儿,就能弄上一大把。自此,走在这里就再也闲不住嘴了。
谷荻吃完了,就盯上婆婆丁的花。婆婆丁就是蒲公英,嫩黄的花儿带上红棕色的花茎,塞进嘴里一嚼,微苦中带着一丝清甜。
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野菜叫做“扁扁叶”,同样是微苦,能嚼出一丝清香。
慢慢长大了,终于能认出开着紫色倒垂灯笼花朵的是党参;知道匍匐在地上握着拳头的,有茵陈,也有卷柏。
连绵的雨后,地上冒出的“粉皮”是地卷皮。洗干净了放在锅里一炒,再磕上俩鸡蛋,味道要比粉皮鲜美得多。多年以后在一家星级酒店吃过这道菜,浅浅的一盘就要六十多块。很多人是第一次逢此美味,不大一会就清盘了。
记得有一次,庄里懂中医会算命的二爷爷路过蝎子岭。他突然停下脚步,指着一株小草对我说,这是小柴胡。从此,我深深地记住了这味解表散热的中草药。
有一位亲戚来我家做客,发现了满岭的荆棵,就让我给她刨上几棵带根的,回去熬药。
岭上有狗奶子,结着橙色的小果。听哥哥姐姐说不能吃,但又抵制不住诱惑,就放在嘴里嚼嚼再吐掉。多年以后才知道,狗奶子就是野生的枸杞。
初秋时节,一种叶子略圆的藤蔓植物会结出绿色的小果。一种表面平滑,一头圆一头尖;另一种略大一些,呈椭圆形,上面有小凸起。这两种小果,我们分别叫它“小瓜瓜瓢子”和“大瓜瓜瓢子”。把绿皮扒开,附在种子上面的是银白色絮状物。放在嘴里轻轻一嚼,清甜可口。直到不久前我才知道,瓜瓜瓢子还有一个尊贵的名字:何首乌。
有一种草,据说有毒,但药效很强。后来知道,它叫附子。也有一种植物叫芙子苗,音同但样子却不一样。浅土下嫩白的根,吃起来清甜可口。
这里还有地黄,因为大人担心我们采摘,就给它取名“打碗花”。打碎了饭碗,就意味着会挨揍。所以,我们谁也不愿去招惹满地的地黄。
带着蝎子满村跑的堂哥,长大后考入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。暑假里我们一起在蝎子岭上玩,他教我辨认很多植物。即便如此,像家雀子盖窝、兔子奶这样的植物,我依然不知道它的学名。离开家乡后,很多植物再也没见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们就在我的记忆里慢慢消失了。
09
有一种细小的匍匐植物,叫“火绳蒿子”。虽然不知道学名,但印象特别深。
那个年代雨水较多,可以说是沟满河平。水多了,蚊子也就多。不过那时候的蚊子很讲“武德”,白天不咬人,晚上掌灯的时候也不咬人。只要一熄灯,屋内的蚊子就冒了出来,嗡嗡作响。
棉线做的蚊帐挡住了蚊子,也挡住了凉风。所以很多人不喜欢挂蚊帐,而是喜欢点火绳蒿子。晚饭后,点上火绳蒿子,一家人都跑到大门口乘凉。熏得差不多了,就掐灭火绳,回屋睡觉。
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用过火绳蒿子,所以就认为冒出的烟会很呛。
有一年夏天,我看庄里的几个奶奶在蝎子岭上拔火绳蒿子,就跟着一起拔。这种草漫山遍野都是,不大一会就拔了很多。其实我只是想帮忙,并不想要。一个奶奶跟我说,她们拔的火绳蒿子,一个热天足够了。让我把自己的带回家去,晾干了拧成火绳熏蚊子。
我带回家去放在天井里,几天就晒干了。父亲下班回家,就拧成了一米多长、拳头粗的草绳。当天晚上吃完饭,父亲就在屋里点火绳。掐灭明火,一股白烟慢慢飘起,一直飘到屋顶。我这才知道,火绳蒿子一点都不呛眼,还带着淡淡的草药香。更为神奇的是,嗡嗡作响的蚊子很快就息声了。晚上撩起蚊帐,睡得特别香。
10
蝎子岭这小小的区域里,不止是植物独特,昆虫爬虫也不一样。比如蚂蚱,这里有一种叫“蹬倒山”,比一般蚂蚱的体型大很多,通体呈浅绿色,油光发亮。大腿很粗壮,末端长着锋利的锯齿。
蹬倒山力气很大,后腿一蹬,就能从我们手中挣脱。这个时候,手掌上会留下点点血印。记得堂弟特别喜欢这种蹬倒山,每次捉住都是爱不释手。有一次他捉到一只,放在盒子里喂它菜叶,居然养了一个暑假。
这里的石龙子,我们称它为“蝎出溜子”,肤色深灰,藏在石缝或者草丛里很难被发现。也只有我们的走过去,它才用最快的速度逃走。
这里最让人心动的是山石釉。这三个字,也只是读音。老一辈人喜欢把牛读作yóu,母牛叫做“shìyóu”。山石釉,一般叫做山水牛。立秋后的第一场大雨,山石釉就突然出现。肥胖的母山石釉在草丛里爬,健壮的公山石釉则在天上飞。雨下的越大,山石釉出来的越多。记得那时候,我们会披上雨衣,挽起裤腿在蝎子岭上捉山石釉。
捉回家后,掐头去翅,放上大盐粒腌上几天。热油一煎,卷在煎饼里吃。人间美味,也不过如此。
11
位于鲁中的莱芜多山,但我们家一带多丘陵,却没有山。站在最高处向四周看,或远或近都是山,整整围了一圈。但最近的山,直线距离也有二十几里。
小时候没见过山,就会想象山就是拔高了的蝎子岭。
有一段时间,父亲在鹁鸽楼水库上班,就把我带了过去。工程指挥部是依山而建的二层小楼,办公室、宿舍,还有食堂都在一起。
那时候有好几个工作人员带着孩子来玩,我就和他们一起在附近爬树摘柿子。这里的山体,是裸露的黄土,间或长着杂草,不像蝎子岭那样有石层覆面,有各种各样的植被。在我看来,这里不过是长着柿子树的大土堆。
那时候我指着高处问父亲,那是什么啊?他说那是柿子树。我说高处是什么?父亲说那是看林的小屋。
其实我要的答案是:这是一座山!这座山叫做云台山,是莱芜的一个著名的风景区,上面有革命圣地和尚洞。
再后来爬过很多山,但都找不到与蝎子岭一样的地表和植被。也只在有人迹罕见的泰山后山,砂石层溢水的地方能看到一些熟悉且又叫不上名的植物。
12
蝎子岭的区域不算小,目测有二十多亩地。往东几百米,是南北走向的排水渠。东岭高坡上下渗的水汇聚在这里,形成一个个清澈见底的小水潭。小水潭大都深可没腰,周边是红褐色的砂石,水底则是乳白色的石层。与周边绿油油的庄稼映在一起,特别漂亮。
在庄稼棵一人多高的时候,来这边的人很少。所以,时常会有獾和皮子、野猁出没。再往东往上,是我们的老林,幽静阴深。所以,家人嘱咐不让我们去那里玩。
蝎子岭往北,是往下的陡坡。沿着羊肠小道走到坡底,是一条河的东岸。这里的土地大都被开垦成农田,原始的坡体变得很窄,一直向北延伸。这就是蝎子岭的蝎尾。
蝎子岭西侧,是五六米高的立壁。再往下,则是间隔两米多的层层梯田。这里的土质都是红褐色沙土,干燥的时候硬如钢板,泡在水里则变成流体。开垦成的农田土质松软,从高处跳下不会摔伤。
所以,我们有时候就从最高处一层一层往下跳,一小会儿就来到河边。
蝎子岭最高处,是“蝎子岭头”。往南,是相对平坦的农田。田边一条宽不过两拃的路,路的西侧是陡坡。坡上长满了红色、蓝色和白色的牵牛花,把小道装饰成花径。沿着小路往南不到百米,就是我的家。
也许是太喜欢蝎子岭,上学时候写作文都爱写蝎子岭。妹妹到外地读书时写了一篇《蝎子岭》,被收录到优秀作文选里。她的老师和同学读后,都想过来看看。
13
蝎子岭的表层和植被都很脆弱,一旦被开垦后,就再也无法恢复。有段时间,附近村庄都种姜。储存生姜需要开凿阴湿且无水的深井,而蝎子岭的地质很符合。于是,几乎在半年间,蝎子岭上出现无数姜井,整个坡面都被掘出的黄土覆盖。洋槐树,还有令人讨厌的臭椿树,趁机在这里撒下种子。多年以后,这里杂草丛生,再也看不到此前的容貌。
后来有一个亲戚从蝎子岭上走,看到满岭的黄土后说,这叫“分蝎子”,预示着你们庄要发达了。
分蝎子,其实是蝎子产子的说法。据说小蝎子从母亲背部生出来后,立刻把母亲的身体吃掉,寓意着推陈出新,预示着繁衍和昌盛。
相信未来可期。而蝎子岭的一草一木、一土一石,早已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,永不褪色。
杨维忠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heshouwua.com/hswsf/9426.html

